2012年12月,作家劉慶邦寫了一篇文章,祝賀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,其中說,“對于中國文學史來說,莫言獲獎具有里程碑意義”。幾乎同時,集美大學中文系講師黃云霞也寫了一篇名為《作為當代文學史事件的“莫言現象”》的論文,“以便為莫言創作的文學史定位確立起某種較為可靠的學理依據”。
莫言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,無疑將被載入中國當代文學史。但從譜系學的視角,當我們談論莫言的時候,莫言從什么樣的傳統中走來,又將引領一個什么樣的文學傳統,在未來的文學經驗中,莫言將如何書寫和被書寫?
莫言來自20世紀新文學傳統
“莫言是八十年代之子”,2012年12月,旅美學者劉再復在《華文文學》雜志發表談話文章中說,他認為20世紀有兩次文學高潮,一次是五四時期,一次是1980年代。“1980年代出現了很多很有創造活力的作家,我覺得他們非常接近諾貝爾文學獎,例如李銳、閻連科、余華、賈平凹、韓少功、蘇童、王安憶、殘雪都很杰出”。
但正是在現今獲獎,令莫言備受質疑,因為文化粗鄙、道德墮落、文學邊緣化,是如今這個時代被貼上的標簽。
“有人不斷地使用這樣的比喻——中國‘現代文學’是好的,是‘五糧液’;而‘當代文學’則是差的,是‘二鍋頭’,這種看起來合乎邏輯的說法實際是幼稚和昏聵的。”2012年12月,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在《文藝爭鳴》雜志發表文章稱。
他認為,文學的演進有自己的規律,它與政治之間,甚至與文化思想之間存在著并不平衡的關系。漢語新文學正是在經歷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壓抑、六七十年代的低谷、八十年代的開放與風云激蕩的新思潮的沖擊,在相對黯淡和沉悶的九十年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成熟。
在張清華看來,如果能將“當代文學不如現代文學”的心態放平,則應該承認“莫言確乎傳承了中國新文學的優秀傳統,并且還是一個發揚光大者”。“也就是說,在莫言獲獎之后,如果說會衍生出一個‘重大意義’的話,那么我以為就是,它會推動改變以往我們對‘現代’和‘當代’文學的割裂的看法,將整個新文學看成是一個真正的整體--從思想到形式、從內容到藝術、從文體到語言是一個自然發育的過程,那么莫言獲獎,自然也是有了一百年歷史的漢語新文學的一個成果,一個發育成熟的標志。”
但他也認為,莫言的獲獎,可以給文學的閱讀和消費帶來短暫的“加熱”效應,但卻難以扭轉整個時代的文化與文學氛圍。這一氛圍,是作家身上的批判性與知識分子性,呈現了漸至稀薄的趨勢。
莫言獲獎的副產品
莫言所受到的文學影響,還繞不過拉美“魔幻現實主義”文學。大江健三郎曾稱贊莫言的作品“是拉丁美洲文學和中國文學融合在一起的非常優秀的文學。”
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滕威介紹,1980年代,隨著中國步入以經濟建設為主的改革開放時期,拉美文學這一“非西方”的、來自第三世界的、中國語境的“小語種”文學竟然掀起閱讀與談論的熱潮,以“文學爆炸”和“魔幻現實主義”為中心的“拉美文學熱”直接影響到中國當代文學的探索與創作,尤以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所受浸染最深。
2005年,四川大學文學博士曾利君完成了其名為《魔幻現實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》的博士論文,其中為莫言專門寫了一節。1982年,拉美作家加西亞·馬爾克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,他的作品迅速譯介到中國,在中國掀起了“馬爾克斯熱”。莫言在閱讀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杰作《百年孤獨》時,一下子被征服了。莫言由此知道小說還有另一種寫法,他當時的感覺,就跟馬爾克斯當年第一次讀到卡夫卡作品時的感覺一樣:“原來小說可以這么寫!”在震驚敬佩、恍然大悟之余,莫言也禁不住躍躍欲試,捉筆操練起“魔幻現實主義”來。
他在1985年推出的那批引人注目的小說如《透明的紅蘿卜》、《球狀閃電》、《金發嬰兒》、《枯河》、《爆炸》等作就是在馬爾克斯等外國作家的影響下所寫出的,其中《球狀閃電》就帶有馬爾克斯作品的印記,為了讓自己的小說看起來更魔幻,莫言甚至在《球狀閃電》中也弄了個粘著鳥翅的怪老頭,讓人不禁想起馬爾克斯的《巨翅老人》。
拉美文學對中國1980年代興起的作家的影響還包括諾貝爾獎。“馬爾克斯是第一個我國與全球同步介紹進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”,滕威說,對于同樣是第三世界的作家,“連嚴肅的《讀書》雜志都是以‘鄰村的張老漢都富起來了,我們該怎么辦’的心態來討論的”。可以說,比照著拉美的諾貝爾獎作家,正是1980年代莫言一批作家的成長軌跡。“包括莫言在內,每寫一部作品,都會有聲音說這是為得諾貝爾獎寫的”,滕威說。
但“魔幻現實主義”的標簽卻被拉美作家自己拒絕。“馬爾克斯在領取諾貝爾獎的答謝詞就是一篇戰斗檄文,是說他的作品寫的就是拉美的現實,而不是魔幻的,來反對西方以理性主義、科學主義的眼光來看待他的作品。”滕威介紹。
1970年代開始,拉美文學已失去了所謂“魔幻現實主義”的現實基礎,在沒有了政治需求后,拉美作家產出的大多是中產階級消費主義趣味的作品。“作為一個整體,拉美文學在世界上的影響也不是特別大了”,滕威說,“只有少數作家還在堅持當年的傳統,比如2011年翻譯到國內的智利作家羅貝托·波拉尼奧 的《2666》,這本小說接續了作家要有擔當的傳統”。
“目前翻譯到國內的拉美文學作品,仍是1970年代以前的作品居多”,滕威判斷,在中國,拉美文學還將掀起一股熱潮,“原因包括2010年,老作家略薩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,2011年國內首次出版了馬爾克斯授權的《百年孤獨》。另外的原因則是莫言的獲獎,對拉美文學的帶動”。
至少在作品上還是知識分子
“面對死亡威脅、外族入侵、社會不公,你如何行動,這是考驗一個人的意志、展示一個人的精神能量的關鍵時刻。莫言對這些關鍵時刻極為敏感,保持著高度的熱情。他的小說,常常把此類情景用夸張手段推向極致,考驗人的忍受能力,拷打人性的韌度,追問人的道德良心。”2013年1月,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國恩在《武漢大學學報》發表文章稱。
但現實中的莫言似乎與作品中的莫言有著涇渭分明的差距,“更愿意做一個作家,而不是一個知識分子”,在他獲獎后談到當年抄寫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這一問題時,開始清晰。
推薦閱讀
書的介質與文明 如果從埃及的莎草紙算起,紙的歷史已經有5000多年了。書寫介質曾經幫助埃及構建了世界上最輝煌的古代文明。 希臘征服埃及后,把帝國的文化中心和最大的圖書館建在埃及,也是因為那個時代最好的書寫介>>>詳細閱讀
本文標題:莫言效應
地址:http://www.geekbao.cn/a/22/20130205/259207.html

 網友點評
網友點評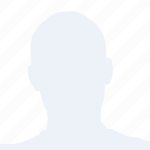
 精彩導讀
精彩導讀



 科技快報
科技快報 品牌展示
品牌展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