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海民:沒有內容做支撐的影響力是不可持續的,是空中樓閣。我們認為《京華時報》在影響力上,當然我們做很多的事情,我們現在品牌也在發力,整個經營也在發力,但是我們自己很清楚,我們一定要在內容建設上下大功夫。內容建設主要是幾個方面,一個是有影響的新聞報道,第二個是評論,第三個輿論監督,第四個主題策劃。我認為影響力主要在這四個方面。先說報道,要在高質量的新聞報道上,我在這里講到高質量是指媒體的報道,它是影響社會的日常手段,也是構成媒體影響力的基本材料。媒體影響力如果是一個大廈的話,它就是由日常新聞報道一磚一瓦建造起來的。日復一日,年復一年,持續不斷的新聞報道所產生的持續的,不斷的影響,它在累積著,加強著媒體的影響力。當然,我們也很清楚,并不是所有的報道都能產生影響,很多報道可能還會削弱影響,比如說那些平庸的報道多了,這個媒體就跟著平庸了,比那些低劣的報道多了,這個媒體也可能低劣了。
在這個時代,由于網絡的迅猛發展,媒體要清醒地認識到,我們現在已經不是缺信息的時候了,你隨便弄一條消息就受到歡迎嗎,未必是這樣,因為大家缺少不是信息,信息泛濫了,爆炸了,甚至過剩了,這個時候,能夠產生廣泛深刻影響的,我認為主要是兩種報道,一種就是獨家報道,一種就是深度報道。獨家報道為什么有影響呢?因為是首先發布的,它可以做到先聲奪人,它是后來信息不斷擴散放大的總源頭。以后不管多少人轉載,多少人放大,它都在擴散著你的影響力,因為你是源頭。這是毫無疑問的。還有一個是深度報道,這種深度報道由于能切中時代發展的脈搏,能夠直擊公眾關注的焦點,敢于觸碰社會發展的難點,容易在公眾中引起強烈的共鳴,從而能擴大你內心的影響力。更多的情況下,在今天,影響力是從這些報道中形成的。這些深度報道反映出一個媒體的新聞敏感度,反映你對事件駕馭的能力,它反映出你鮮明的立場,同時反映出你的品格。這種影響力會不斷地放大。
第二個方面,影響力要在觀點鮮明的評論上下工夫。剛才提到《京華時報》的評論,確實這幾年來下了大的力氣,我們認為這是《京華時報》這兩三年來改版最重要的一步,因為《京華時報》在過去初創辦前幾年是不說話的,甚至是連創刊詞都沒有的一份報紙,就只講事,不說話。那個時候是行得通的,因為那時候大家還缺少信息,現在大家不缺少信息,缺少的是觀點。這個時候你再不說話,就是一個啞巴。我們從2008年年底持續改版時就提出來評論是媒體高高舉起的一個旗幟,是媒體向周圍世界發出的聲音,那么他也是媒體擴大自身影響力的思想高地。在今天資訊發達,信息爆炸的時代,受眾所缺少的已經不是信息,而是對信息的選擇、理解、分辨、消化。這些消化需要觀點來指引,特別需要評論。而且信息接受得越多,就越是需要評論,同時今天又是人人都是麥克風的時代,眾說紛紜,讀者也需要在雜亂的噪音中,分辨出那些主流的聲音,分辨出那些最令人信服的權威觀點,這些就是時代的強音。《京華時報》要在這方面下功夫。
正是基于這么一個認識,我們花了兩到三年的時間,現在構筑了《京華時報》完整的評論體系,同時構筑了京華時評這個觀點高地,一個高地,一個體系,這個體系包括時事評論,財經評論,文娛評論,教育評論,包括各個專業領域的評論,比如房產、汽車、健康領域的,旅游等等,在各方面都在發聲,體育也在發聲,這樣一個體系已經構成了。再一個特別是構筑了京華時評這個品牌觀點高地,從不說話的報紙,到天天要說話,而且要敢說話,說真話,也要會說話。有很多重大的問題,北京的,全國的,乃至世界的問題,我們都發聲,這塊的例子很多了,比如關于北京的地鐵禁報令,連續發九評、十評,比如關于廢除強拆,我們連續發五篇評論,關于上海大火發了多次評論。最近幾期評論,大家印象也很深等等。特別是在有的時候,我們很多兄弟媒體覺得不好講話,不知道該怎么講話的時候,《京華時報》及時地發出了評論。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新疆“七五”事件出來以后,這個太突然了,而且太重大了,背景又太復雜了,這個時候要不要發篇評論?第二天全國的媒體只有三家發評論了,是人民日報、新華社,還有《京華時報》發了。三篇評論,《京華時報》的評論最好,標題也非常醒目,“穩定是福,動亂是禍”,直截了當,旗幟鮮明。我聽人大新聞學院的老師給我講,現在我們的很多評論已經成為人大新聞系評論課的范文。在北京我遇到各層次的讀者,特別是高層次的讀者,他們現在是每天必讀京華的第二版。
周曉鵬:讀者已經形成閱讀習慣了,或者有閱讀的預期在里面。就像您說的,現在在做網絡媒體我感覺到,大家獲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越來越多樣化了,在這樣一個時代,大家除了每天看發生了什么事之外,還是有很多人更想了解這個聲音意味著什么,對我代表什么,對我有什么影響,我怎么去看這個事,這些成為很多讀者的需求。從這種意義上講,評論的份量,觀點性內容的提供就變成很重要的課題。
吳海民:對。評論是媒體影響力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,為什么重要呢?因為它能夠從思想上左右公眾對社會的認知和判斷,而且由于這些評論所代表的是媒體機構的立場、觀點,就更能夠形成影響力。同樣是一篇評論,講了這么一個觀點,如果你從個人博客當中發出的,當然有些意見領袖也很有影響,但他畢竟是個人意見。但是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媒體,這個觀點是京華時報講的,代表一個新聞機構的立場,它就更有力量了。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可以說評論上不遺余力在做,而且下一步還要再加強。比如說財經評論,我們現在是每天在財經版頭版做一個資本論,每周有一個評論專版,下一步就是每天有一個評論專版,財經評論要做評論專版,讓各種觀點在《京華時報》的各個版都能夠散發出來。
影響力第三個方面是輿論監督。輿論監督這個問題稍微敏感一點,但是我們認為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運用媒體的力量對社會,對政府事務,社會事務及其他涉及公眾利益的事務進行主動干預,促使他們沿著法治的軌道和公共準則運作的一種特有的權利,這是媒體特有的權利,也是擴大媒體影響力的利器。我們現在的監督應該說也是一個體系,包括黨內監督,人大監督,司法監督,群眾監督等等,這是一個監督體系,在這個體系當中,輿論監督是不可或缺的,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。輿論監督有它特殊的辦法,比如說它特有的公開曝光,公開批評這種方式,能夠產生很強的影響力,甚至是一種震懾力。在任何情況下,我們的媒體都不能放棄這個批判的武器。如果一個媒體放棄了輿論監督,缺乏批評精神,失去報道中和評論中應有的鋒芒,那就很難談得上影響力了。在這個問題上,《京華時報》是非常堅定的,是一貫的。昨天我們在審片,就是《京華時報》十年的視頻,我們自己制作的,這個視頻回溯了《京華時報》的創刊號,創刊號的頭版頭條是什么?就是輿論監督,密云水荒問題,在當時是北京各個媒體都不敢報的題材,但是又影響到整個北京市民的生活用水,所以《京華時報》創刊號第一篇報道,第一個頭條就是輿論監督,一直堅持到現在,我們覺得應該代表市民,應該反映他們的呼聲,關心和維護他們的利益,應該替他們說話,對不公正的事情,我就是要打抱不平,對錯的事情,我敢于講,讓你改正。剛才我講評論的時候,講到我們的九評地鐵禁報令,那是非常典型的,我認為這是中國媒體輿論監督的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,我曾經想讓評論部把報道的整個過程寫出來,這是非常有趣的。北京市一道禁令,不允許地鐵一號線、二號線賣報紙,這種事情固然有它的理由,就是交通擁擠,影響秩序。但是地鐵本來是公共場所,也是一個文化場所,你走遍世界,哪個國家地鐵不賣報呢?我到日本去,大家都坐在那里看書看報,到歐洲去更是這樣。歐洲這么多年來,報業的一個新的趨勢就是地鐵報。你說在中國的首都不讓賣報,這個事情我認為明顯是錯的。問題是你要是真的為了維護安全、緩解擁擠,咱們也能理解,問題是它還留了尾巴,即只允許一個報紙賣,就是娛樂信報,這就不公平了,如果說這份報紙與北京市沒有關系,也行,但是恰恰這份報紙和自己有利益關系,這就太失公平了。所以《京華時報》在這些問題上,不管你是哪個高層做的決策,堅決要進行監督。所以當時我們派出記者到現場,進行了詳細地調查和報道,同時發評論,九評,一直評到你收回成命為止。從第一天起就把九評的題目都擬訂好了,我當時估計九評能解決問題,事實就是這么巧,當第九評出來的當天下午,北京市緊急開會,廢除了這道禁令。我認為這就是輿論監督的力量。
推薦閱讀
環球網記者王欣報道,在5月25日舉行的中國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,國防部發言人耿雁生指出,廣州軍區的解放軍根據訓練的需要,為提高部隊的網絡安全防護水平而設立了網絡藍軍。國防部方面于5月26日對本網獨家回應稱,網>>>詳細閱讀
地址:http://www.geekbao.cn/a/22/20110528/7246.html

 網友點評
網友點評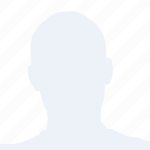
 精彩導讀
精彩導讀



 科技快報
科技快報 品牌展示
品牌展示